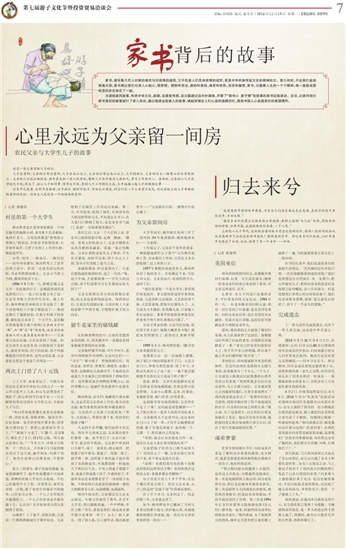这是一沓父亲写给儿子的信。
儿子在贵阳,父亲的信寄往贵阳;儿子在乌江边上,父亲的信寄往乌江边上;儿子到浙江,父亲的信又一路攀山涉水寄到浙江。父亲给儿子说庄稼收成、猪牛养生和一家人的身体;嘱咐儿子在外面为人要和气,学习工作要用心。读书时,父亲担心儿子在学校吃不饱;毕业了,担心儿子和同事、领导处不来;等到儿子工作稳定之后,又开始操心起儿子的婚姻大事……
信笺早已发黄、信封多有磨损,信中病句、错别字很多,字体也不漂亮,但它们是一个父亲望子成龙、对远离故土的儿子牵肠挂肚最好的见证。信的主人是德清一中的杨再辉老师。
|记者徐敏霞
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
杨再辉老家在贵州省松桃县一个叫岩脑壳的偏僻山村,家有8个兄弟姐妹,他排行老五。父母虽然都是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民,但把读书看得很重,尽管条件艰苦,只要子女到了上学的年龄,都送进学堂。
小学,初中,一路成长,一路付出……初中毕业那年,杨再辉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。但高二还没有读完的时候,母亲突然得病离去。父亲又当爹又当妈,继续供他读下去。
1986年8月的一天,松桃县城又是五天一次赶场的日子。县城最热闹的老电影院门口,一张大红喜报公布了这一年县里考取大学的学生名单。榜上有名,杨再辉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了!整个决基坳村六个寨子都波动了;一条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,在寨子和寨子间传播:我们这里也有了一个大学生,是岩脑壳那贱家第五那个娃娃(父亲的名字叫“贱”,而“那”是“哥”的意思,这是淳朴的苗族人对人最亲最近的称呼)……父亲那天也在赶场,父亲也看到了喜报。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,回到家放下菜担儿,就赶往村前,村子的前面,那个叫扳鹰咀的河坎竹林里,是母亲的坟墓,父亲要赶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……
两次上门借了八十元钱
上了大学,离家更远了。可做父亲的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自己的儿子——担心学习赶不上人家,担心生活费没有了饿肚子,担心和同学们处不好……只在解放初期读过两年小学的父亲,开始给儿子写信。
“和同学相处要像在家里兄弟姐妹一样,团结友爱,尊敬老师。勤读苦学,打好基础。家里的事情不要多想,没事就不要回信了,要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。”“猪娘下小崽了,下20只,存活8只,现在卖了5只,得172元钱。明天就去给你汇钱。”“今年天旱,洋辣子只收得一千三四百元。古历6月1日起到现在没有下过大雨,抽不到水,田都干死了。你的生活费已经准备好,不要担心。”
读大三的那年,寨子里流传猪瘟,家家的猪都死了,地里的菜遭遇干旱加冰雹,贫瘠的村寨几乎没什么收成。年纪已经拖得不小了的二哥要娶亲,家里仅有的一点钱,除了寄给在省城读书的他外,已经水尽山穷。一个儿子在学校里不能饿肚子,一个儿子的亲事也不能再拖下去。怎么办?从不轻易求人的父亲想到了借钱。
向谁借?上下寨子、苗族汉族,大家这一年都跌跌撞撞日子都不好过。父亲想到了在城里工作的远房亲戚。第二天,早早起来,赶到了城里,从来没有向人借过钞票的父亲,不知道怎么开口,在人家门口徘徊了很久,还是没有勇气敲门,真是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”。
离开之后,父亲一个人在街上走,穿着自己做的轮胎草鞋,走得一脚深,一脚浅。看看太阳快落山了,父亲才硬着头皮再次摸到亲戚家。亲戚一家正吃晚饭。父亲红着脸说家里儿子娶亲,手头有点紧张,周转不过来,借个百儿八十的,等谷子红苕收了就马上还。
亲戚犹豫着,但还是答应了。只是在把钱递给他的时候,说了一句话,“唉,这个年成,大家都艰难——手里头的这点钱,孩子们说要买自行车都说过好几回了!”
父亲头低得比对方的肩膀都还要低,但父亲还是将钱接过来。钱借到以后,父亲没有直接回家,父亲在街上人家的屋檐下坐到半夜,才慢慢往寨子的方向走。
猪牛是家里的储钱罐
在给杨再辉的信中,父亲经常提到家里的猪、牛,因为猪和牛一直都是农村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。
父亲称呼猪不叫猪,叫牛不叫牛,甚至叫鸡鸭都不叫鸡鸭,父亲叫它们——“养生”!像小孩子一样地照顾它们。每次进家,菜筐里,箩蔸里,粪桶里,衣服口袋里,总能摸出几块破洋芋、干瘪的包谷或是几个在地里已经埋得带了酒味的红苕。这些都是家里鸡鸭的零嘴点心,这些零嘴点心,连圈栏里的猪和牛也都有份。
杨再辉说,好多回,他睡到半夜里醒来,总是看见父亲的床上空着,枕头尚有余温,靛青染蓝的家织粗布铺盖掀在一边。父亲的声音从屋子后面传来,“养生,先将就点,等新红薯下来,再给你们饱顿子嗛!”
人家的牛住草棚,他们家的牛住瓦房。每年冬天到来之前,父亲都会把牛栏修葺一遍。而平常日子,父亲只要一有空,就会给牛收拾。父亲把牛牵到村口大树下,端上一盆清水,细心地用一把铁篦子给牛梳毛、篦虱子。每篦一梳子,就手臂一挥,这样篦下来的虱子就抖到放了水的脸盆里,牛虱像划船一样地划几下然后沉下去。牛身上的虱子都篦下来,连虱子卵也篦干净了,牛就轻松了,牛就浑身油光水滑像是穿了一身的缎子衣服。牛睁着两只亮晶晶的玻璃球一般的大眼睛望着父亲,充满感激,充满温情。
每回牛犊出栏,父亲都比卖儿卖女还难受。牛犊已经被穿了鼻环,在买牛人手里,四只脚抵着地,一声声呼唤,不肯上路。“养生,莫说是你们,就是崽女都不能守着爹妈一辈子!去么!跟人家去。到了别人家,自己要听话,做活路要着实……”父亲跟在后面,一路将小牛送出寨子。
为父亲留间房
大学毕业后,杨再辉在贵州工作了一段时间,94年来到德清,继续他的本行——当老师。
工作稳定了,父亲在千里外的老家,一厢情愿地期待儿子找个“父母都有退休工资、全家都有工作的、又善良又本分的姑娘”,过上体面日子。
1997年暑假结束没有多久,杨再辉结识了他的妻子。关系确定下来,写信告诉父亲。父亲很高兴,收到信的当天,就回了信:
“现在你谈得一个是大学生,爹看到信很是高兴。爹又想到你这些年来到处奔波,又是贵阳又是德清,又是你的两个妹,又是你爹我,把你年纪都等大了。儿只要女方不嫌你,你莫嫌人家,只要她工作好品格好。爹希望你把你的事落实好给爹来个照片和信爹都高兴极了。”
买房子准备结婚,父亲写信问他,你们要买多大的?装修大概要多少钱?我把家里的猪卖了,给你们汇来够不够
……
1999年5月,杨再辉结婚。10月份父亲来德清看儿子。
他领着父亲一层一层地爬上楼梯,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来开了门。父亲立在门口,伸着头朝里张望,望了半天,才转过头来对儿子说:“崽——我千想万想都想不出你们房子是这个样子喔!”
进家,换鞋。父亲生怕他脚步走重了会将家里的地板踩破,生怕走得不稳会滑倒。父亲小心翼翼,走着,打量着,电视柜看看,橱门看看,沙发看看。
走到装有穿衣镜的墙前,父亲停住不走了。“爹!这间就是给您睡的……”儿子指点着有一张单人床的书房给老人看。父亲跟着儿子走进书房,走出来时在门口立了好一阵,才用手去触摸眼前的墙,摸了发现是面镜子,就再摸一下,又摸一下,然后就自己笑起来:
“哎哟,我还以为里面是另外一家,我还以为是人家在那边朝我们看!”
父亲把镜子里的自己都当成别人了!房间里走了一圈,父亲在客厅沙发坐下来,坐下来还是抬头打量:
“崽耶!怕我们那里的县级干部都没得你们这样的房子噢!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,爹做梦都会笑醒喔!”
房子其实只有八十多个平米,在这个城市算是小的了。但在父亲看来,儿子已经是比“县级干部”住得都还要好。
住了半个多月,父亲回去了。回去的第三年,父亲就去世了。
如今,杨再辉也早已搬离了当初父亲来过的那个地方,但在他心里,在最隐秘的情感世界深处,他一直还为父亲留着那样的一间房……